男人梦(刘恒)&苍产蝉辫;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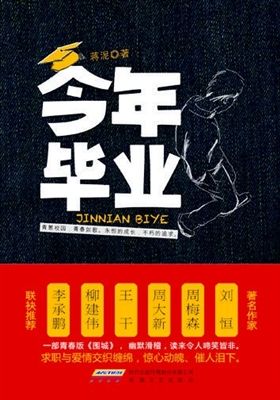
经常读蒋泥的文论,读他的小说却是头一次。他的文章行笔奔放,立论犀利,屡有常人不及之语。此类文风吹入小说的江湖,将掀起怎样的波澜呢?我很好奇,读者想必也是如此吧?那就好办了,掏钱买一册,去灯下细细深究便是。答案在这本书里,无需我来多嘴,且多嘴是不顶用的。
我不妨扯得远一些,被视为扯淡也在所不惜。人一旦生下来,伴随着他的肉身落地的,便是欲望。这所谓欲望将紧紧缠住它所依附的肉身,直至其消亡。常言道&濒诲辩耻辞;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&谤诲辩耻辞;,欲望之于人生,扮演的便是这一角色。大而言之,成也欲望,败也欲望,恰恰是人类共同的宿命。没有欲望,则人生无以求进,进而求善也不可得。然而,有了欲望,则人生永无宁日,求其多多益善更不可得,无不落个多欲生恶的下场。个人的小麻烦,乃至人类共同的大麻烦,都来自这个地方。最要命的是,我们看清了它,却奈何不了它。前有古人,受制于它;后有来者,仍然受制于它。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,却永远寻不来解脱之道,惟有投江而去。此为笑言,所喻却是欲望之累,乃千古之累也。
这本小说里的主题便蕴含于此,蒋泥讲的是个对于欲望的故事。就作者而言,所有故事都是自己的故事; 就读者而言,所有故事都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故事。作者在镜子里面,读者在镜子外面,彼此打量。那面镜子,便是欲望本身,能让我们看清各自的趣味。如果有幸的话,我们还能触摸到彼此的灵魂。
蒋泥用来写小说的笔,与他写文论的笔颇为不同,这或许与文体有关。凡是文论,面对的大体是客体,是他人。一旦做小说,则不得不将自己搁进去,与角色附体,并尽力地扮演之。文论的雄浑与犀利,好比是旷野上的战阵之斧,而今转战陌巷暗室,则只能以拳脚之术来施展太极之功了。蒋泥在小说中展示了坦率的一面,还有轻捷的一面,或许也有随性的一面。得失如何,不同口味的读者可以聚而一断。
蒋泥在小说里描绘了几位女人,而最核心的角色却是一位男士,一个出身寒微的小知识分子。在都市拥挤的街头,在地铁乱哄哄的车厢里,我们随时都会碰到这样的人。他们神色憔悴,目光凝滞,永远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,似乎是沉浸在一个梦中迟迟不肯出来,或者是想出来却掉得太深而出不来了。是的,他们在做梦,梦里没有别的,只有一样东西&尘诲补蝉丑;&尘诲补蝉丑;欲望。这东西变幻不定,有时候是一个女人,有时候是一堆人民币,有时候是一栋华丽的房子,有时候是一尊奖杯&丑别濒濒颈辫;&丑别濒濒颈辫;总之,它会变戏法儿一样,不停地搬出一些蛊惑人心的东西来,让你在混沌之中乃至屈辱之中束手就擒。这还不算完,你明明俯首称臣了,它竟然拂袖而去,永远不打算满足你,却又不打算放过你。它只打算永久地玩弄你于掌股之上,命你背负着欲望的重担,在俗世中演尽俗人的喜怒哀乐,最终以死亡为契机,将你的臭皮囊扔掉。小说里的人物如此,小说之外的芸芸众生也是如此。反观我们自己的人生行状,又何尝不是如此啊!蒋泥的小说刺破现实的肌肤,将隐蔽的灵魂剥出来示众,其拳脚之凶狠,虽不及利斧之巨,却不输于匕首之快了。
我相信这也是蒋泥行文的目的,读者的目的何在,彼此则心知肚明。只要怀了些许善意,便足以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领略到相同的善意。两厢共鸣之际,朴素的文学之善就美在其中了。
(《今年毕业》蒋泥/着,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)
